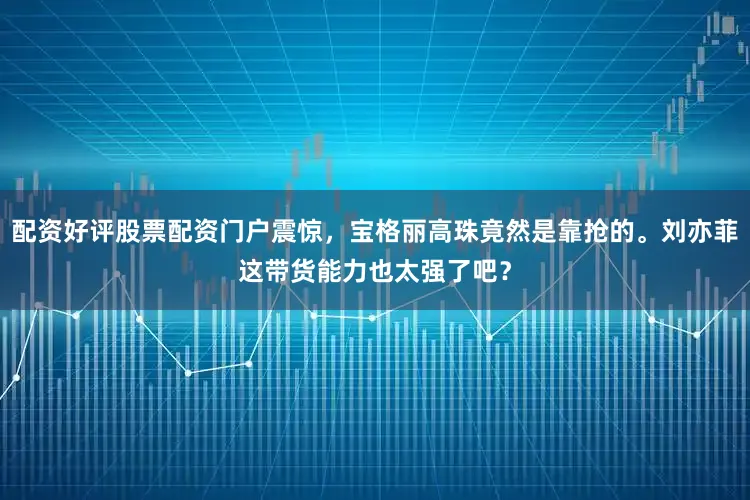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江门五邑地方组织高举抗日旗帜,团结带领五邑人民及全世界江门籍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共御外侮、毁家纾难、血战到底,用热血与生命筑起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为展现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战壮歌,在全市营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浓厚氛围,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统筹江门日报社、江门市广播电视台、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推出“江门抗战烽烟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媒体报道”,敬请垂注。
抗战期间,在众多回国参战人员中,有一群有技术的南洋青年,承担了打通滇缅公路“抗日输血管”的重任,其中已确认有158名五邑籍南侨机工英勇参与。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成为五邑籍华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中国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蜿蜒在横断山脉纵谷区,海拔500米至3000多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湍流,令人心惊动魄。满载军火物资的卡车行驶在如此险峻的路上,稍微不慎,便车毁人亡。在这条路上开车,要抱着必死的决心。南侨机工要闯过山高河深路险关、雨天泥泞塌方关、路窄车多摩擦关、瘴病疟疾夺命关、抛锚无援饥寒关、日机轰炸关,九死一生,才能打通这条“抗日输血管”。
展开剩余90%今天
我们一起了解
滇缅公路上五邑籍英雄的故事
李月美:
女扮男装报名应征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191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她自幼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从小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内心深处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七七事变爆发后,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李月美和同学们上街卖花,将募捐款项交给南洋筹赈总会,支援祖国抗战。
“得知南侨总会招募机工时,李月美非常激动。她模仿古代‘木兰从军’,女扮男装报名应征。”李月美的大儿媳尹凤娥在海南琼海与记者连线时介绍。
滇缅公路大部分是土路,道路崎岖,地势险恶,每逢下雨更是泥泞不堪。遇到道路塌方或者车子抛锚时,李月美就得将车停在荒山野岭,食宿没有着落,还要看管好所运物资,防止遭到野兽袭击。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李月美常常晚上关掉车灯,连夜疾行,确保物资及时运输至前线。
1940年5月,李月美在一个急转弯处不慎翻车。当时,海南籍南侨机工杨维铨正好路过,他把李月美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送往医院急救。两人因此相识,结为了夫妻。
“后来婆婆把这些事说给我们听,我们觉得好浪漫。”尹凤娥回忆道。
李月美女扮男装支援抗战的事经媒体披露后,一时间轰动海内外,她被誉为“当代花木兰”。廖仲恺夫人、著名社会活动家何香凝女士为她题写了“巾帼英雄”四个大字。
身体恢复后,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机工卫生所的一名护士。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心护理、照料在战争中负伤的抗日将士,并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以热情的歌声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亲切接见了李月美。
陈寿全:
忠孝不能两全
陈寿全,1918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一个华侨家庭。
“1939年,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和南侨总会的组织下,年仅21岁的父亲热血沸腾,报名参加了第八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然而,爷爷、奶奶坚决不答应,舍不得他离开家,去炮火连天的战场。父亲在说服不了爷爷奶奶的情况下,毅然背着家里人,悄悄报名。他说忠孝不能两全,盼望他们能原谅自己的不孝。”陈寿全的女儿陈玉姗回忆说。
当时,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可以报销归国路费,但是陈寿全想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更需要经费,于是悄悄地卖掉了家里的小汽车,自己花钱买票,踏上了归国的征程。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奔忙在这条随时都有可能车毁人亡的滇缅公路上。
一天晚上,陈寿全的汽车在一片树林旁抛了锚,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嗡嗡作响,根本无法修车。他只好紧闭车门,在又闷又热的驾驶室里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开始修车,但仍然被蚊子叮得周身起红点。陈寿全忍饥挨饿一天多,开车到达昆明时,浑身时冷时热发起疟疾来。幸好他是在昆明病倒,医疗条件相对好一些,如果是在路途上病倒,恐怕就没命了。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于疟疾。
有一次,陈寿全的军运车开到半山,突然雷雨交加,山洪暴发,右边山崖上磨盘大的石头朝下乱滚,左边悬崖下浊浪翻腾。面对如此险情,车绝对不能停下,他只好驱车冒险前进。过了险区,陈寿全浑身瘫软。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一天,有一辆车连司机带军火一同翻下了悬崖。
还有一次,遇到几架日机轰炸扫射,就在离陈寿全的车不远的公路上,几辆车被机枪射中引起军火爆炸,车毁人亡。陈寿全的车也差一点中了日军的枪弹。
“父亲对自己的事讲得不多,但我们兄弟姐妹都知道,父亲及其战友是在极其险恶的滇缅公路上英勇地从事抗日救国的崇高事业。”陈玉姗说。
后来,惠通桥被炸,机工解散。陈寿全到三江电化冶炼厂工作,毕生报效祖国。
罗洪:
“初一跌落,十五才能返上来”
罗洪(祖籍新会),1910年出生,年轻时为谋生去了新加坡。1939年,他与好友陆汝金(祖籍鹤山)相约,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
滇缅公路地势险要。罗洪曾说:“初一跌落,十五才能返上来。”在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良溪村,罗洪的儿子罗振侠、外甥周权法向记者讲述了罗洪的故事。
“我们曾经重走滇缅公路。经过‘老虎嘴’等地,沿途确实惊险崎岖,父亲说得一点也不过分。何况机工们是驾驶着满载援华物资的汽车出入崇山峻岭,同时还要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穿行,真是九死一生。”罗振侠说。
南侨机工驾驶车辆行驶在“老虎嘴”。
据罗振侠与周权法回忆,罗洪曾跟他们讲过一个过桥的故事:化装混入难民之中的日军特工,正伺机偷袭占领桥梁。当时有一名商车老板在桥头倒车堵住了交通,他不听从指挥还骂人,被守桥卫兵开枪鸣告。一声枪响,日军特工做贼心虚,以为被发现了,马上开枪应战,桥上乱作一团。在现场的罗洪马上协助指挥车辆加大油门尽快冲过去,民工也争先恐后地逃散开。
通过到云南实地考察,罗振侠与周权法认为,罗洪所讲的过桥故事与惠通桥战事相吻合。1942年5月5日下午,中国军队提前炸桥,成功地阻塞了敌人的西进通道,把日军堵在了怒江的对岸。
“这是罗洪保存的两枚徽章。”周权法拿出两枚徽章给记者看:一枚上面铸有“美军驻中国印缅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部”字样,另一枚上面写着“华侨互助会会员证章”。他说,从第一枚徽章来看,罗洪曾被抽调到“美军驻中国印缅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部”工作,应该是属于技术熟练且英文水平过硬的人员。
邝金源:
久行24天死里逃生
1914年,邝金源(祖籍台山)出生在马来半岛吉礁(吉打)亚罗士打。1939年,邝金源偷偷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邝金源常常在寒冷多雨的清晨赶往雾气弥漫的24道拐、黔桂公路、盘江铁桥抢修发生故障的卡车:有水箱破裂的、有发动机乏力的、有钢板折断的、有离合器失灵的……如果是汽油耗尽而走不动,他还得为卡车送油。最危险又耗时的是要把坠落深谷的车子吊到路面上来,而且还要搜集散落四处的军用物资,如汽油、子弹、枪支等,再帮忙搬运回站里。邝金源的后人曾这样复述邝金源说过的话。
1942年,邝金源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1942年4月29日,日军出动大炮十余门,装甲车、战车三十几辆,在飞机掩护下,向腊戍发起猛攻。13时许,腊戍失守。
后来,邝金源家人在整理其物品时,发现一张他的照片。上面写着:“于腊戌36里被敌包围18个钟头,久行24天到保山。”“在敌人的炮火中走出来的我!”“不忘24天路程悲恨!”显然,邝金源用这张照片作为特别的纪念,而他的两位战友却不幸牺牲。
在另一张照片上,邝金源写着:“吴进步同志在第三批服务团,在敌人进(攻)腊戌时,他在运输抢运时被敌包围了,牺牲了,在刺刀至(之)下亡,为国争光!1942年5月。”发黄的照片,被邝金源用绿色的相角仔细地护好,深切而隐忍的悲痛从一笔一画中流露出来。
1946年,邝金源复员返回马来亚。1993年1月22日,邝金源去世,享年79岁。
陈爵:
闯了三次鬼门关
陈爵1919年出生在马来亚。他的祖父陈傅万祖籍广东赤溪县(现台山市赤溪镇),于1865年到南洋谋生,之后克俭拼搏,在当地成为经营橡胶园和锡矿的业主。
1937年,日军侵华。陈爵忘不了祖父的教诲:“我们人在异国他乡,可心是中国的、情是中国的,任何时候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华侨的根在中国。”
1939年5月,陈爵成为南侨机工。受训1个多月后,陈爵被混编在西南运输处第五大队当一等驾驶兵。日军即将侵占广西柳州时,他受命把榕县物资和一台大车床运送到贵州遵义再回昆明。当时广西即将沦陷,从柳州撤退的战车、炮车、军队与逃难的百姓混杂在公路上,导致交通严重堵塞。车只能艰难地一点点往前移,四天四夜还没穿过贵阳。为了不打瞌睡,他常把头浸进车上备用的水桶里提神。沿途缺吃少喝,陈爵饿得一点劲都没有,遇到一处卖饭的,就大口大口往下咽,之后肚子疼痛难忍蜷缩在车上不敢动弹。
1942年,陈爵从昆明送军队去畹町,沿途见到多处被炸的尸体。尸体在太阳暴晒下奇臭难闻,忍不住要呕吐。成群的乌鸦,还有苍蝇在尸体上饱食,其惨状目不忍睹。日本侵略中国的实际罪证,激发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到了保山,陈爵腹泻不止,车上的军医给他打针吃药也止不住。听说大烟土能止痛止泻,有人用罐头与一个老乡换了一点大烟土,他吞下后果然好些了。把军队送到前线后,他又从畹町装上一车汽油回昆明。
还有一次去畹町,突然大雨滂沱,陈爵在泥泞中驾车时浑身发冷,忽而又发起高烧,感觉到头昏眼花。他努力地挣扎着,费力吞下奎宁丸,抚摸着护身符昏睡过去。“十疟九死”,后来要不是路过的机工把他从车里拖出来,送到医疗所,那满是泥浆的卡车就成了他的坟墓。
抗战胜利后,陈爵加入了中国劳动协会和全国总工会,在哈尔滨离休,安度晚年。多年以后,陈爵的妻子王兰贡帮他整理回忆录,保留了这段珍贵的记忆。
梁伯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父亲是23岁回国参加抗战的。当时,二伯开了一间机修厂,父亲在二伯厂里帮忙。后来,父亲听说祖国召唤华侨青年回国抗战,于是不顾大伯、二伯反对,报名加入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从此,父亲与大伯、二伯断绝了联系,只跟姑妈保持联系。”目前,生活在台山的梁伯添之子梁承恩向记者介绍。
据梁承恩回忆,梁伯添曾说过,他开车很快,一般是别人已经开了半个小时,他才开始开。梁伯添之所以抗战胜利后没回马来西亚,是因为日军飞机炸断桥梁、袭击车队和人员,他的护照和其他证件都放在车上,被毁于炮火中,所以他回不去,也无法办理复员和领取奖金。
机工队伍解散后,梁伯添因为在国外长大,能够与盟军的人沟通,于是他先后当上了翻译员和排长。抗战期间,梁伯添因为工作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他也都去过。
对于回国抗战当机工这个选择,梁承恩说,父亲认为很正常,正所谓“舍小家为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62年,梁伯添在海南省澄迈县仁兴农场结婚,1968年回到老家台山都斛镇河旧村务农。1986年7月27日,他因中风去世,享年70岁。
据不完全统计,在滇缅公路沿线,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南侨机工献出了生命。 1000多个日夜,平均每一天都有一位南侨机工倒下;10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平均每一公里都长眠着一位南侨机工的英灵。
“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南侨机工用生命、鲜血与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书写了荡气回肠的一页。他们怀赤子之心、秉家国之念,在捍卫正义与和平、追求民族尊严与复兴的道路上,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发布于:北京市股票配资哪家好,青海配资开户,石家庄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